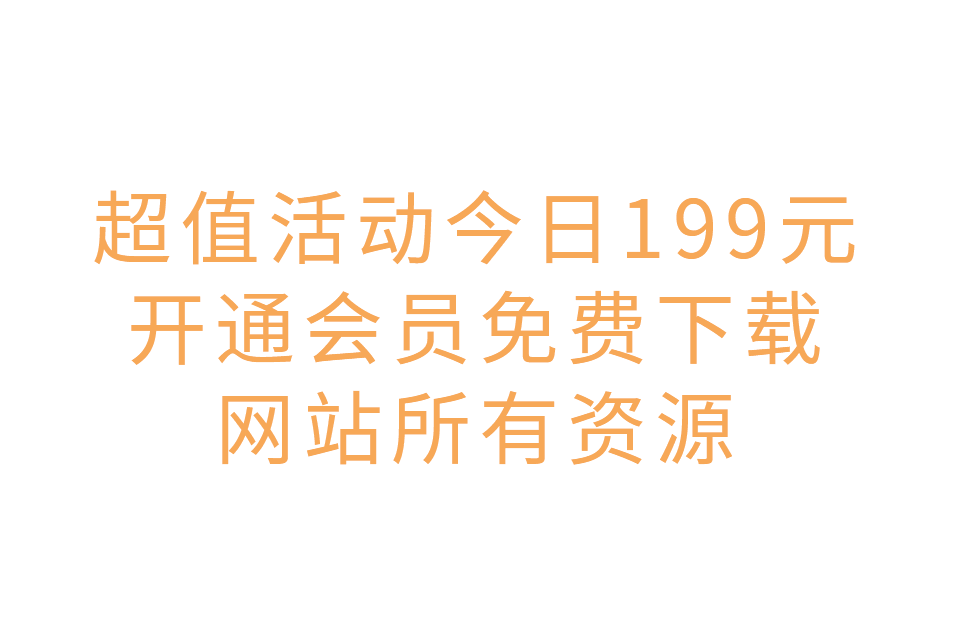鲁桓公二年秋,“公及戎盟于唐,修旧好也。”
明显,这个旧好是指鲁隐公时期的“旧好”,即鲁隐公二年“春,公会戎于潜,修惠公之好也;戎请盟,公辞。”同年,“秋,盟于唐,复修戎好也。”而鲁隐公时期的“旧好”乃是鲁惠公时期的旧好。可谓是传统盟友关系!用今天的话来说,这是要把老一辈领导人缔结的传统友好关系,代代相传,发扬光大啊。
前后两代鲁国国君,即位后必须处理,而且摆在头等位置的双边关系,就是鲁国和戎人的关系。都是在即位后的第二年会盟并与之续签盟约,这样的“戎”,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,有怎样的特殊重要性,才会有这么大的“面子”?到鲁桓公,戎人与鲁国的友好关系最少已经维持了三代人,不可谓不长!
戎人与鲁国的关系,如果拿来和宋国的关系相比,就更加耐人寻味。鲁国与宋国也是盟友关系,更是姻亲关系,鲁隐公、鲁桓公两人的母亲都来自宋国。但是,这样的甥舅关系,也是说翻脸就翻脸。鲁隐公十年,鲁国联合郑国、齐国差点肢解了宋国。这说明,定了盟约,结成甥舅之国,维持友好关系也不是一劳永逸,自然而然就能够世世代代的。这说明,戎人和鲁国的关系,其稳定程度,其重要程度,犹在宋国之上。
两国关系,不光要经受时间的考验,还要看能不能经得起大风大浪。鲁国与宋国的关系明显就经不起考验。但是,鲁国和戎人关系就能经得住风浪的考验。比如,鲁隐公七年,周天子派凡伯到鲁国“来聘”。这当然是一次非常隆重的访问,首先,周天子派人“来聘”,这份尊荣就很高;其次凡伯作为使者,规格也很高。凡伯自己就有封国,又同是姬姓,和郑庄公级别一样,伯爵。但是凡伯访问鲁国之后,就在归国途中被戎人打劫了!即所谓的“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。”这样重大的事件,竟然没有任何后果!鲁国没有找戎人讨说法,凡国也没声没响,周天子更不用说,没有任何表示!这足以说明,鲁国与戎人关系的特殊性!
这个“戎”是一个西周诸侯国吗?这是后世很多人的看法。但没有文字证据,也缺乏考古依据。和鲁国结盟的“戎人”,在鲁国的地位着实特殊,不像是附属国,更像是鲁国有求于“戎”。鲁隐公时期,有小国来朝,比如滕侯、薛侯;有大国来聘,如齐侯、周天子。但似乎戎人没有这份闲心。同样,各国之间的讨伐,尤其鲁国参与甚至牵头的军事行动,戎人也很超脱,未见其参与。尤其,鲁隐公十年,鲁国、齐国、郑国发起的讨伐宋国的战争,应该说就在戎人的眼皮子底下发生,尽管戎人与鲁国结盟在先,但也不参与。这说明什么?说明戎人与“众”不同!过着与华夏诸侯不同的生活,和鲁国之间存在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盟约!这就是说,戎人可能不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家。
更加直接的证据在于,鲁国与周边国家结盟,或者共同出兵讨伐,不论是《春秋》还是《左传》,或者称齐侯、郑伯,或者称邾子、许男,但是戎人与鲁君会盟,一律都称戎人。类似“戎人”这样的称谓,按照《左传》解释,在各国活动中,如果国君不出面,仅由其他大臣代劳则称为“人”,所谓“微”人,即级别低的人。鲁国国君出面,而戎人首领不出面,这几乎不可能。因此可以断定,戎人没有封号,也不论封号,但首领是存在的,势力范围也是存在的,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!
细查鲁国与戎人在鲁桓公二年的这次盟会的记载,还有比较特别的其他地方。比如“九月,入杞。公及戎盟于唐。冬,公至自唐。”这说明,鲁桓公伐杞之后,便到达唐地与戎人会盟,直至冬天才从唐地返回。唐地据考证就是棠地,应该是在今天鱼台县附近。鲁桓公这次秋天去,冬天回,历时应该在前后一个月左右,为什么这次会盟要这么长时间?是发生了什么变故?还是另有隐情?参考鲁隐公二年与戎人的会盟记载:“秋八月庚辰,公及戎盟于唐。”就可以看出,鲁隐公与戎人会盟在秋天,日期很具体,但却没有鲁隐公返回的记载。为什么同在唐地会盟,前后国君记载不同,这必有原因。
这个秘密也许就藏在紧接其后的记载中。即“冬,公至自唐,告于庙也。凡公行,告于宗庙;反行,饮至、舍爵,策勋焉,礼也。特相会,往来称地,让事也。自参以上,则往称地,来称会,成事也。”这段解释性的叙述,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要记载鲁桓公回国的问题,但其实更让人怀疑鲁隐公这次出行可能遇到了麻烦!为什么呢?
其一,鲁国君主从鲁隐公到鲁桓公,多次出行,各有记载,但多数不记载回国一事,这次有何独特之处?
其二,鲁桓公这次出行回国,按照《左传》记载,要到宗庙“饮至、舍爵,策勋焉,礼也”,这说明,鲁桓公回到宗庙,吃喝结束,放下酒爵,就开始论功行赏了。这是“脱难而返”的感觉。
其三,这次鲁桓公与戎人会盟,属于“特相会,往来称地,让事也”,可见鲁桓公不仅仅和戎人是平等会盟,还存在“让”事。至于“自参以上,则往称地,来称会,成事也。”这是说,三个国君相会,则去的时候称会盟之地,回来的时候称会盟之会,以表达会的重要性。这在前述《春秋》记载中,并无成例。
一个大胆的推论就是,戎人和鲁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,这里面存在不平等的因素,而且一定是鲁国让着戎人。比如这儿的戎人原来属于游牧民族,风俗与华夏民族殊异,但却是鲁国这个地方的原住民。鲁国等华夏民族东来后,开始从事农耕生产,挤压了原住民的生活领域,但由于双方生产方式不同,人口不多,还存在互相学习互惠互利的关系,因此能够长期共处。但由于鲁国的影响,这儿的戎人已经逐步脱离游牧民族的生活,开始逐步定居。这里的戎人,应该在语言、风俗、装束上与北戎、山戎、犬戎大致相同,不然,古人不会把这些民族统统归于“戎”人。
古人注疏者认为,戎人与鲁国东方的莒国都属于风氏、己姓,是太皞之后。估计是想把这些民族统统归纳在炎黄子孙的名下。但这种想法很难得到考证。莒国与戎人不同,是实实在在的西周诸侯国家,莒国不但有国君世系,也有大量出土文物佐证。但可以确认的是,莒国也是不奉周礼,文化民俗也是自成体系,而且可以肯定的是,莒国来自古东夷国,是原来山东半岛上的主人。因此,把戎人归于东夷族存在一定的想当然。这种想当然,又忽视了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在记载民族类型时具有的准确性。可以肯定的是,古人不会把八杆子打不着的民族在称呼上归结为同一个称呼,这也是太小看古人了。
“戎人”为何在鲁国很特殊?因为他们是这块土地的原住民,这是其一。其二,戎人是游牧生产,和鲁国的农耕文化具有互补作用。其三,戎人人口不少,具有比较强大的战斗能力。其四,戎人虽然是游牧民族,但文化上并不落后。其五,戎人在今天的山东曹县附近生活,是宋国与鲁国之间的强大存在,戎人对鲁国存在一定的军事防护作用。其六,戎人不尊华夏之礼,不参与诸夏之争,因此诸夏也不好与之计较过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