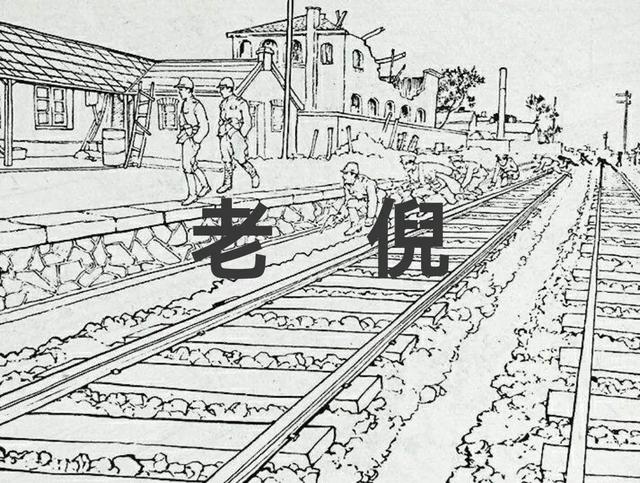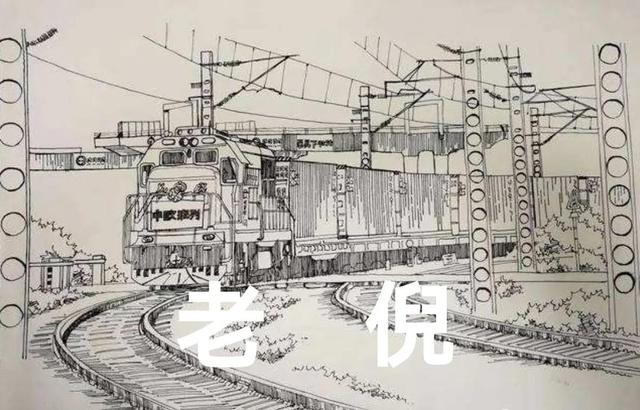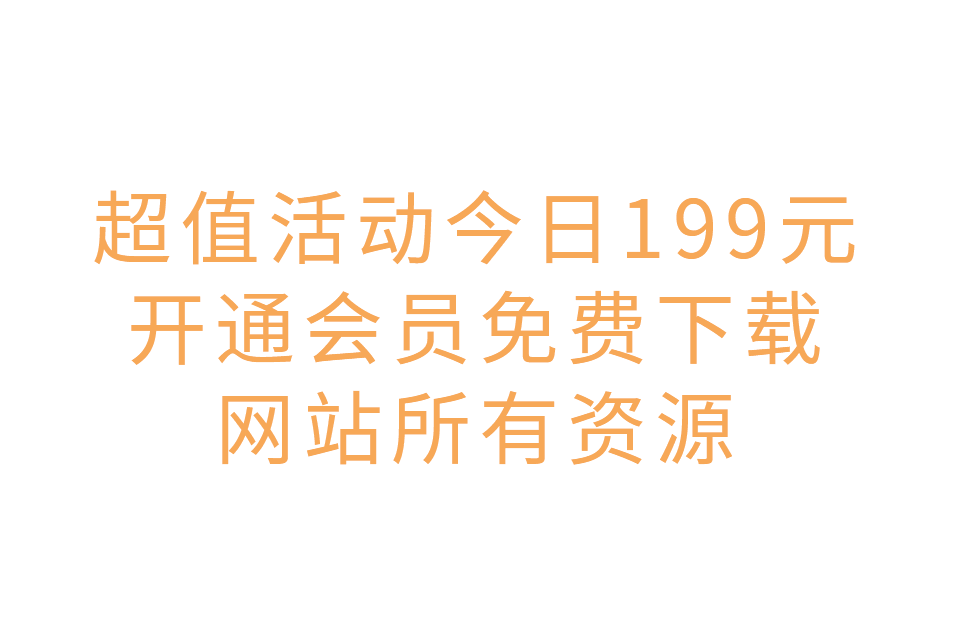倪忠田和列车段的一部分运转车长整体转岗到客运段干列车员,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应。
他们这一批运转车长,一共有十几个同事选择到客运段,他是年龄最大的。
由运转车长变成列车员,首先是岗位工资也发生了变化,比过去低四档,一下子就少一、两百元。一些伙计不愿意了,联合起来去找客运段,到路局上访。最后,为了安抚他们,客运段在请示路局后,也采取一些过度性补助措施。而且,客运段列车员档位工资虽然比运转车长低几档,但绩效工资、安全奖、补票奖等乱七八糟加起来,比过去干运转车长工资高许多。这样一比,大家的心里也算平衡一些。
从列车段转岗到客运段,两者最大的不同就是:运转车长是静,列车员是动。运转车长是单独作业,在工作中无人说话;列车员是群体作业,而且对旅客有说不完的话。
干了几十年的运转车长,倪忠田已经习惯一个人在诺大、空旷,甚至有点幽暗的守车里,座在瞭望窗上的台子上,有时坐在能够看到远方的靠窗铁椅上。随着列车行驶,守车不停地、有节奏地晃动着,让他昏昏欲睡,或陷入遐想。
一个人在守车上呆久了,他不喜欢交流,害怕面对陌生人。

在运转车长时期,只要是倪忠田执乘,他会很在意守车里的卫生环境,喜欢他的整个世界都是洁净的,整齐的。他妈妈是个医务工作者,每时每刻都十分注重干净、整洁、卫生。她对家人和孩子也要求极严格。
倪忠田从接车那一刻开始,整个守车就是他的领地,也是他的世界。
他会把乘务包先放在乘务值班室,然后拿着扫把、抹布,不紧不慢地把守车里面的地板、座椅、瞭望窗,还有守车外面的走廊、踏步、扶手全部清扫、擦抹一边,直到满意为止。
如果是冬天,他还会到值班室提上满满几筐煤块,把守车里的炉子里烧得旺旺的。再把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拿出来,放在炉板边上加温。整个守车会温暖无比、香气四溢。
倪忠田实际上是一个思维丰富多彩的人,但他的表达能力永远跟不上他的想象力。
倪忠田还有一个不愿意承认的弱点,就是胆怯,害怕与人交流,更喜欢一个人独处。这与他幼年时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
倪忠田父亲倪大树出身在贵州遵义大山深处的寨子里。云贵川那边的男人身材普遍矮小精瘦,但倪大树却长着一副高大、强健的身板,一脸的络腮胡。很多人都会以为他是山东人或东北人。

一九五一年,解放军进贵剿匪时,倪大树在寨子里给地主放牛耕地 。他看见住在寨子里的部队穿得好,吃得也好,就跟着部队参军出来了。
后来,他所在的部队整建制改编为铁道工程兵六师,赴朝鲜修建铁路。回国后,六师又轰轰烈烈参加宝成铁路建设。在一次施工中,已经是排长的倪大树因为在施工中去救战友而摔下悬崖,身负重伤。也就是受伤住进甘肃天水的师部医院,成就了一段英雄爱美、美女仰慕英雄的姻缘。铁道兵小排长倪大树和野战医院护士长、高小毕业生胡志英相爱,并最终结婚生子。
美好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,然后就是无休止的拌嘴、吵架、呕气。倪大树常年在铁路工地作业,养成了粗犷豪放的性格,加之没有文化,使他与身材纤瘦,思维丰富的妻子胡志英交流越来越困难。特别是胡志英连生了两个女儿,倪大树的心情更不好了;胡志英也被工作和孩子磨的精疲力尽,温柔全无。倪大树好不容易从宝鸡工地回来探家一次,热乎不到两天就开始吵嘴,一直吵到倪大树返回工地。
特别是胡志英性格高傲,孤僻,对生活标准要求高,对卫生要求严;而倪大树是大老粗,几近文盲。每次回来,胡志英都让倪大树先去厕所把里里外外的衣服全部脱下来,放在大木盆里用开水浇上去烫,还要大肥皂把身体从头到脚洗干净才算完事。一开始倪大树不习惯,争吵了好几次,无奈还是遵从了胡志英的要求。

有了倪忠田这个儿子以后,倪大树的心情比过去好多了,但胡志英的情绪比过去更糟了,几乎到了无法工作的地步。
胡志英申请转业回老家,被安排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医政科工作。两年后,倪大树也转业到妻子所在的城市,他选择了到铁路工务段工作。
倪大树和胡志英无休止地吵架,也给几个孩子在心理上带来了很大阴影。他们每一次吵架,几个孩子都吓得躲在小屋里,手足无措、瑟瑟发抖。
一开始,街坊邻居还来劝架,时间久了,大家也习以为常了。隔一段时间不吵架,邻居们就会开玩笑地问小忠田:“你爸妈怎么没有吵架啊?”气得小忠田眼泪直流。他恨透了天天吵架的父母,他恨透了看笑话嘲笑他的邻居们,他恨透了父母生了自己,让他在街坊邻居面前丢脸。
父亲和母亲不停地争吵,孩子们感到特别无助。那时候,倪忠田不想要自行车,不想要手表,不想要新衣服。他最大的愿望只想要一个温暖不吵架的家。
也就是这些原因,倪忠田落下了不喜欢与人交流的病根,他总认为低人一等,总以为别人在嘲笑他。
倪忠田虽然性格懦弱个头不高,但他继承了母亲漂亮面孔,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的相貌也更加英俊了。当时,他在铁路机械学校上学时,就有“机校唐国强”美称。

春季的一天早上,倪忠田执乘一趟货车回来,出了车站检票口,老远见一个脚边放着一个大行李袋的女孩,一边焦急地翻着挎包里的东西,一边不停地抹着眼泪。
一种男人的同情心让倪忠田不禁停下脚步:“小同志,怎么回事啊?哭得这么伤心。”
女孩子一看眼前站着一位穿着铁路制服的工作人员,一屁股坐在行李包上,哭得更凶了:“我坐这趟车去省城教师培训班报到,可是火车票半路上弄丢了,怎么也找不到了。这可怎么办啊!呜……呜……”
倪忠田一股助人为乐的大义气概涌上心头,他俯下身子,轻轻拍着女孩子:“不要急,我先送你进站上车。如果在车上找不到车票你就补一张好不好?”
女孩儿被这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态度感动了,连忙说好。
倪忠田顾不上执乘一夜的疲劳,一手掂起姑娘的行李包,一手拉住姑娘的胳膊,急匆匆往进站口方向走。
进站口的工作人员和倪忠田很熟络,倪忠田向他们招招手:“我亲戚急着赶车,上车补票啊!谢谢!”
来到站台上,倪忠田又和站在车门口验票的列车员说了一句什么,拉着女孩上车,安顿好座位,又把她的行包放在行李架上。

这是一趟始发车,他抬腕看看手表,离开车还有几分钟。
“好了,你就踏踏实实坐在这里啊,停三站就到省城了,不耽误你去报到。”
女孩早已没有了焦急,一脸笑容地看着倪忠田:“同志,要不是你帮忙,我肯定要误车。怎么感谢你呢?”
“应该的,应该的。举手之劳。”
“我月底培训班结业后回来一定要请你的客。怎么找到你呢?”
倪忠田看着她笑,把车窗打起来,伸出脑袋向列车前端指了一下:“你看站台边上那一栋楼就是我们单位。我是运转车长。”
女孩也随着他把头伸出窗外,就在这一瞬间,倪忠田闻到女孩身上散发出特有的芳香,顿时令他心脏狂跳不止,脸上一阵发热。
女孩缩回身子,露出惊诧地表情看着他:“你这么年轻就是运转车长了?车长一定很厉害吧?”
倪忠田说:“怎么说呢,就是开出去的车都归运转车长管。”
女孩说:“那我以后坐车就找你了啊。有没有联系电话呢?”
倪忠田想了想,从制服上衣内口袋里掏出手帐本和笔,潇洒地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列车段南线车队值班室电话,然后把这一页撕掉地给她:“你就说找倪忠田,他们会告诉我的。”
女孩兴奋地说:“我叫雷春花,今年刚分配到市五小当老师,这是去省教师培训班进行上岗培训。等我回来时一定找你啊!一定!”
列车开出很远,倪忠田依然站在站台上久久没有离去。他喜欢上了这个女孩,是谈恋爱的感觉。